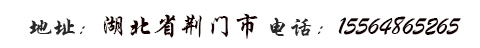随笔我的爷爷
|
我在很努力地想这个老头的样子,因为隔着厚厚的坟包,我真的快记不清他的样子了。 印象中,他的身材高大瘦扁,腰背又弯又驼,走起路来颤颤巍巍,头发稀疏花白,头顶的头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脱落的只剩下光滑的头皮。要是趴上去细看,上面那几根银白色的头发像是镶上去的。他总是带着黑色的毡绒帽,若是在拄着棍仗,像极了封建社会大家长。可不是,要是看到我和妹妹穿牛仔短裤,少不了一顿挨骂,说不得体。他呢,总是爱穿着带领子的衬衣,胸前的领口总是不扣扣子,干瘪枯瘦的皮肤总是一展无遗。这倒让他和封建大家长不合了。有时,能看到他骨瘦嶙峋的胸腔。强迫症的我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扒拉他的衣领,希望能让它们整齐些。爷爷总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随意自在,倒像是“济公活佛”。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那一年,爷爷才八十六岁,一直身体硬朗,夸自己从不吃药的他,因去田地里看麦苗的长势而摔断了大腿。卧床三个月,他躺在床榻上,眼窝塌陷,人体骨骼清奇可见,让原本就瘦骨嶙峋的他,显得更加憔悴。弥留之际,去看他,他颤巍巍地伸出胳膊,用力拉着老公的手深情地说:“我最不放心就是这个孙女了……”这是我俩最后一次的见面,这个历经沧桑岁月磨难得老人,还没有享受过子孙的福就走了。 这个老头,从未见他偷闲过,不是忙活他北地的菜园子,就是编他的桑树树篮子,或者修剪他种的桑树。身上总是沾满了泥土,像个老顽童。你要是有时找不到他,只要去菜园寻他,一定可以寻到。不过你要对这菜地,大声吼几嗓子他才能听到。记得,小时候我常趴着家里的墙头,或者常跑到地头喊他。曾因不理解他,埋怨他,吃饭不知道回家。他总是乐呵呵一笑盖过。后来,我也成了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时,也废寝忘食。懂得了爷爷,弓着腰不辞辛苦的快乐。 他还有一爱好,就是爱喝酒,亲戚好友只要来,必喝。不过从未见他醉过。他是一个精明能干的老头,小时候邻里八乡红白喜事都会请爷爷,记忆里爷爷穿着干净的中山外套,口袋里露出他带的白色毛巾,笑脸相迎着前来吊孝的宾客,礼貌而又周到。爷爷还干过各种小生意,游过乡,走过店,也结交了好多挚友。曾因半夜做一个梦,梦见在南乡结识的挚友,瞒着我们一个人骑着三轮车走了二百里地去找他们。那时的他已经快快八十了。知道后,我很是震惊,也不理解。责怪他,要是出事可咋办。问爷爷为什么这么远,这么大岁数了一个人去找他们,爷爷说,就是想见他们一面。他们老一辈的友情,应该是最为真挚的吧。 每当谈论他的过往,总是意气风发,意犹未尽。这个历经磨难的老头,依旧乐观,仁慈。虽过着最为平凡琐碎的人间生活,却有着最丰盈的人生。 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母亲在爷爷菜地那,盖了一间老年房,和父亲住在那里。老房子还在,门口的那棵老槐树也在,只是修了新的柏油路。那片菜地也在,只是种了不同的菜,可再也没有爷爷种的豆角,白菜,萝卜了。桑树由于没人会修剪,再也没有结过我爱吃的桑葚了。老房子上再也没有爬满南瓜藤了。 一切似乎没变,一切好像都变了。 时光荏苒,斯人已逝,生者如斯,生者长思。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aijiaoa.com/zyhj/13339.html
- 上一篇文章: 雨兰原创植物美文楷树,楷书得名和它有关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