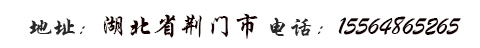柴禾与炊烟
|
西安市秦川中学闫军海 在中国北方一些农村地区,柴禾(cháihuo)指的是能燃烧以提供热量的树枝、秸秆、杂草等。在我居住的西北地区,人们又常常把这些柴禾分成两种:一种叫“硬柴”用于生火造饭,指的是生长在沟塬壕岸边木质比较坚硬干枯的树根、树枝、树梢等。一种叫“穰柴”用来烧炕,指的是庄稼地生长的秸秆、藤蔓等。 硬柴不同于硬菜。硬菜,意思是指吃饭时,比较解馋的,实惠的,抗饿的,美味的,用大块的肉类炒的菜,比如酸菜炖排骨、辣子鸡丁和夫妻肺片等。硬菜与吃有关,而硬柴与灵魂有关。硬柴是草木之精华,是自然美的浓缩,是草木一生最好的姿态,是温柔灵魂坚硬的核心,她绚烂过,圆满过,丰盈过,最后把自己活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今年前些日子,村卫生室为年满70周岁以上享受高龄补贴的老人年检,趁着年检这个时间,我带着母亲回了一趟老家,老家门里门外树根檐下那一堆堆寂寞的柴禾,墙角椽头那一圈圈蒙尘的蜘蛛网,让我想起了很多关于它们的往事。 凡是在农村长大的人,最熟悉不过的就是那石棉瓦苫着的土厕,以及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一株株迎风生长的柿子树、枣树、核桃树,他们或倔强或纤细或亭亭玉立地站立在老家一方属于自己的天空下,慢慢地成长着,更熟悉的是那堆放在台阶一角的硬柴,人们每天都从她们的身旁走来走去,伴着烟囱升起的炊烟,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普通的日子。当离开农村以后,我才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昔日的村庄那炊烟和硬柴是一道最美的风景。 在院子里站了很久以后,我慢慢地蹲下身子,轻轻地捡起一根短硬柴,静静地放在掌心,感受着它瘦骨嶙峋的身躯,心想,它们曾经也有过灿烂金黄的颜值,有过挺拔伟岸的身躯。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看着窗台之下那被浓烟熏得乌黑乌黑的炕眼,我发现,窗台上锈迹斑斑的双面斧,已经好久没有人使用了,斧面上厚厚的尘土无言地诉说着岁月剥蚀的故事,这让我想起了父亲。 父亲退休以后,全部的岁月都是在这充满烟火的日子里度过的,这满屋子的硬柴气,烟火味,最能撩动我的心。 北方农村的冬季是寂静而漫长的。母亲长年卧病床褥,不废汤药,到了冬季特别怕冷,每天要烧三次火炕,甚至三伏天还要生火烧炕,为了温暖家的土炕熬过年后漫长而料峭的二三月,父亲跑遍了老家的沟沟坎坎坡上坡下,拉着一辆年久失修的架子车,拿着斧头,常常与五伯和亮亮他爷走遍了沟塬坡渠田间地头:老壕边、猫儿窝、南头的水渠岸、北头的庙门前,都留下了他们刀凿斧砍的痕迹,一斧头一斧头地挖着深埋在黄土中的树根,无论是椿树、槐树、杨树,还是梨树、苹果树、梧桐树等,在他们的眼里都是可以生火做饭烧炕的好柴禾,是硬柴,然后一截截据断、一根根挖掘、除土、装车,一车车搬运回家,堆放在门前,在寒冷的冬季,父亲与这些硬柴共同做着一个温暖的梦,在他的心底或许还有一个更为隐秘地只属于他自己的奢侈而遥远的愿景。 农闲的时候,父亲就开始劈柴。常常经过整个中午的辛苦,他劈柴劈得累了,就把双面斧放在砧木上,燃起一根香烟,坐在小马扎凳子上,看着家里屋檐下摆放的整整齐齐的成垛成垛的柴禾,就像看见自家粮仓里冒尖的粮食、水瓮里平口的井水一样,心里觉着踏实了许多。或许在这时,他还做着一个和大堰河同样的美妙的梦。 硬柴是乡村的灵魂,炊烟是乡村的语言。 夕阳西下,天麻麻黑,又到了各家各户做晚饭的时候,缓缓地炊烟从混着饭香的老屋升起,宁静而轻盈、缥缈又虚无,缠绕在老家庭院的树梢上,各家各户烧炕的青烟,也袅袅娉娉地生了起来,爬过南墙,升上屋顶,随着晚风,飘到原野的上空,慢慢地,慢慢地与暮色聚拢交融成灰蒙蒙的一色,如烟似雾,进入到人们的梦香之中。天寒地冻的村庄,似乎也因此世俗了许多,温暖了许多,人性了许多。 “咳咳……咳咳……咳……咳咳咳”,从浓烟弥漫的炕眼处传来父亲烧炕时粗粝而浊重的咳嗽声,那声音一声接着一声,一声重过一声,声声让人揪心,阵阵使我痛心。 这是父亲在烧炕。满脸满手灰黑的他,或蹲,或坐,或半跪在炕眼门口,把那些早已或抱,或用粪笼提前弄回来烧坑的柴禾放在粪笼边,用一根炕耙,伸进乌黑的炕洞口,把炕洞里的余灰推平。如果炕洞内的余灰太多太厚,他就用碎铁锨掏出来一部分,放在簸箕里,然后,再把剩下的灰,用炕耙推开抹平。因为炕洞内的余灰,不能掏得太净,要留有灰底子,否则,浪费了很多的柴禾不说,炕,是怎么烧也烧不热的。 等炕洞里的灰收拾好了,他再往炕眼里填塞进去一些几天前早已晒干碾碎的玉米杆,或玉米芯子与麦草,有时,还有从院子里清扫整理出来的树枝与树叶。用玉米杆或长一点的树枝烧炕的时候,会依着柴禾的长相,顺长,依着炕洞内的纹理尽量舒舒服服地塞进炕眼,让每一把柴禾都填塞到位。 然后,用我和弟弟写过的废旧作业本或报纸引着火,等星星之火蔓延起来以后,再用扇子一下一下连续不断地扇风,等炕烧好以后,再在上面撒上耐火的潮湿的锯末或刈子(碎柴草末混合着细土,阻燃而又耐烧的一种东西),来煨炕。目的是让柴禾不要燃烧得太旺太快,炕火慢慢燃着,才能保证整个晚上炕都是热的。等到这一切都收拾妥当的时候,他就完全变成了一个黑人,两个鼻孔都被灰尘熏黑了,连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浓烟伴着暮色在咳嗽声中定格成为一桢桢永恒难忘的画面。 每每这个时候,屋里屋外,墙角砖缝,整个院子都弥漫着柴禾烧过后那种特殊的人间草木的味道。 下意识里,我就习惯性地把目光投向了厨房,当年,母亲也曾扎着围裙燃起灶火,蹲坐在风箱前,膛火映红母亲的脸颊,她把一根根柴禾添进炉膛,为一家人的生活操心忙碌着,额头的汗水和着铁锅里的水声滋滋作响。等我吃完早饭上学去的时候,身后,云淡风轻,炊烟袅袅,母亲又开始用马勺舀水喂猪,洗衣,摘菜,做饭,一把把地撤下麸糠喂养满院撒欢的三只小鸡了。 寻常一样窗前月,便有柴禾更不同。这些柴禾如同门外槐树下的草木一样,也曾向阳而生、天然恬淡,默默无言,有过生命最纯净朴素的一面,而今,栉风沐雨,阅尽了岁月的沧桑,依然将自己最美的姿态呈现于我们的眼前。记得汪曾褀说过,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柔。的确,柴禾跟花儿一样,都是灵魂的。 如今,十年过去了,寒来暑往,草木荣枯,老家之所以是老家,不仅仅是因为门口有两棵国槐,还有屋角檐下成垛成垛的柴禾。这些柴禾静静地在檐角墙根黙黙地呆了十年,没有人打扰它们,是它们自己静静地朽掉了。 十年间,家里发生了许多事,我和弟弟也都结婚生子了。记得孩子过满月的时候,我们请来了服务队,想在家里热闹热闹,也让父母开心开心。这样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父亲多年积攒的成堆的柴禾就能派上用场了。当我去掉断砖,掀开蓬布,拿起粪笼,露出柴禾走近服务队主事时,主事满脸的不理解,鄙夷地说“这些柴禾早都用不上了。现在有的是煤、气、电,节能又环保,绿色引领时尚,呵呵!”听完这话,我拿着瘦瘪灰黑的硬柴的手真的感觉到很轻很轻,那硬柴没有一丝重量。 离开老家,转身锁门的时候,从门缝里突然传来几个声音,我分明地听到窗台上的那把双面斧对我说,当第一斧砍在硬柴上的时候,你是看见了。粪笼说,当惊蜇的第一声雷响的时候,你是看见了。风说,当霜打柿子的时候,你是看见了。是的,柴禾与炊烟的往事,我是真的看见过。 年5月18日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aijiaoa.com/hjyx/8730.html
- 上一篇文章: 投票进行时候选名单已揭晓快为你心目
- 下一篇文章: 转角遇见绿看看这些家门口的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