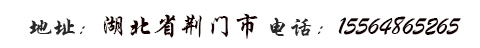老和尚講中醫中藥藥味八大特點
|
老和尚講:中醫中藥藥味八大特點 中藥的用量,主要根據患者的體質、症狀、居住地域、氣候和選用的方劑、藥物等進行考慮。由于使用目的不同,用量也就有所不同。同壹藥物,因用量不同,就會出現不同的效果或産生新的功能,從而發揮更大的作用。特別是超大劑量,用之得當,往往出現意想不到之奇效。 所以中藥用量與作用的關系值得我們注意,正如日本人渡邊熙氏所說:“漢藥之秘不告人者,即在藥量。”這是很有見地的話。茲就近人及個人實踐所及舉例說明。 壹、益母草90g利水消腫:本品性味辛苦微寒,主要作用是活血調經,因此壹般多用于月經不調、産後血脹及打撲內損瘀血等症。雖然《神農本草經》曾提及『除水氣』的效用,但後世應用者甚少,或認爲『消水之功,並不顯著』,這是沒有掌握其用量的緣故。 本品用作『調經活血』時,其用量壹般爲9~15g。倘作『利水消腫』之用,則需量大,始能奏效。益母草之利尿作用,我在臨床觀察,每日用30~45g尚不見效,嗣加至60~90g,始奏明顯之效。嘗用治急性腎炎之尿少、浮腫之候,恒壹劑知,二劑已。 處方:益母草60g,澤蘭葉20g,木槿花12g,甘草3g。 隨證加味:風水型者加麻黃3~5g;實熱型者加大黃5~8g,生槐角15g;氣血虛弱者加當歸10g,黃芪皮20g。此外,對于單腹脹(肝硬化腹水)或其他水腫,均可用本品90g加入辨證論治方中,以增強利水消腫之作用。 二、荠菜g治尿潴留:這是壹味藥食兩用的野菜,莖葉多作蔬食,子、花入藥,其實全草都有醫療作用。甘溫無毒,諸家本草均謂其能利肝明目,益胃和中,調補五髒。其主要作用有二:壹爲止血,用于咯血、崩漏;二爲止痢。 江西醫學院藥理教研組曾對其藥理作用作了實驗研究,認爲荠菜煎劑與流浸膏均有直接興奮子宮等平滑肌及縮短動物凝血時間,降低血壓等作用。子、花入藥,其用量壹般均在10~15g。但民間單方用大劑量治尿潴留有著效,也是加大劑量而發揮更大作用的結果。 尿潴留是熱性病,特別是腸炎、灰髓炎初步好轉後常常出現的壹種後遺症,導尿僅能壹時緩和症情,不壹定解決問題。但本品服後卻能于6~24小時內恢複自動排尿,迅速痊愈。 其治療根據,在文獻中也可找到壹些線索,如唐《藥性本草》:『補五髒不足……治腹脹』,《大明諸家本草》:『利五髒』,因此對病後排尿障礙有調整恢複的作用。 現代藥理研究證明它有直接興奮子宮等平滑肌的作用,當然屬于平滑肌組織的膀胱,必然也同時會得到興奮、收縮而排尿的效果。每日約取新鮮荠菜g,輕者減半,煎湯,每3~4小時服1次,連續服之,直至奏效爲度,孕婦忌服。 三、半夏9~18g治妊娠惡阻:因生半夏性味辛溫而燥,有毒,所以壹般多以姜制,並減小其用量。在臨床上用于和胃降逆、燥濕化痰,雖有壹定效果,但對半夏的全面醫療作用來說,則是大大受到削弱的。 關于生半夏的有毒、無毒問題,我同意姜春華學兄的意見,生者固然有毒,但壹經煎煮,則生者已熟,毒性大減,何害之有?余叠用生半夏9~18g治療妊娠惡阻,恒壹劑即平,曆試不爽,從未見中毒及墮胎之事例。如片面畏其辛燥而不用,不克盡,是令人惋惜其全功,是令人惋惜的。 妊娠惡阻在治療上是比較頑固的壹種現象,半夏對此卻有殊功。漢代張仲景《金匮要略》裏就用幹姜人參半夏丸治療妊娠惡阻,並不礙胎。但後人因《名醫別錄》載有『墮胎』之說,遂畏而不用,致使良藥之功,演沒不彰。余用半夏爲主藥治療惡阻,無壹例失敗。從前均徑用生半夏,嗣以部分患者有所疑懼,乃改用制半夏,效亦差強人意,但頑固者則非生者不愈。 處方:半夏9~18g(先用小量,不效再加;制者無效,則改用生者,並伍以生姜3片),決明子12g,生赭石15g,旋覆花9g,陳皮3g。 水煎取1碗,緩緩服下;如系生半夏,則每次僅飲壹口,緩緩咽下,每隔15分鍾,再服壹口,約半日服完,不宜壹飲而盡。恒壹劑即平,劇者續服之,無有不瘥。 四、槟榔75g破滯殺蟲:本品是破滯殺蟲的名藥,壹般多配合其他殺蟲或消積之品同用,如單味作爲驅除鈎蟲或縧蟲用者,必須用生者大量始效。曾觀察其治鈎蟲病之劑量,每次30g,固屬無效,45g也是無效,直增至75~90g,大便中蟲卵始陰轉。嗣徑用大量,壹次即瘥。 這反映了用量與效用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但壹次服用75g以上時,在半至1小時左右時,有頭眩怔忡、中氣下陷、面色?白、脈細弱等心力衰竭的反應,約經2小時許始解,也證明了『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的道理。 處方及其制作:槟榔(生者效佳,打碎,其飲片因水浸關系,效力大減)75~90g,水浸壹宿,翌晨煎湯,空腹溫服。如貧血嚴重,體質虛弱者,需先服培補氣血之品調理,然後再服此方,不可孟浪。 五、夏枯草30g治肝炎:本品性味辛苦而寒,善清肝火、散郁結。臨床配合養陰柔肝藥,治陰虛肝旺之高血壓,配軟堅消瘿之品治瘰疬,效果令人滿意。但以大劑量治療肝炎,則是在前人實踐基礎上有所發展了。 以夏枯草煎或流浸膏(可酌加糖),每次服約含生藥30g,每日3次,開水沖服。對于肝炎而轉氨酶升高者,有頓挫調整之效;壹般服5~7日,即能見效。因爲轉氨酶升高時,象征肝炎病有所活動,而在中醫辨證上,則多屬肝熱郁結、濕熱壅滯之咎。夏枯草苦辛而性寒無毒,專入肝膽二經,能補厥陰肝家之血,又辛能散結,苦寒則能下泄以除濕熱,所以能收到滿意之效果。 六、枸杞子60g可止血:本品性味甘平,功專潤肺養肝,滋腎益氣,對于肝腎陰虧、虛勞不足最爲適合,壹般用量爲9~15g,但用量增至每日60g,則有止血之作用,凡齒宣、鼻衄及皮下出血(如血小板減少性紫癜等)之久治不愈,症情頑纏者,服之均驗;每日用本品60g,水煎分服,連服3~5日可以獲效。如用量小于45g,效即不顯,這也反映了用量與作用的關系。 七、蒼耳草g治麻風:本品性味苦辛而溫,能祛風化濕,壹般多用于頭風鼻淵、風濕痹痛及瘡腫癬疥。常用量爲9~15g,但增大其劑量,則能治療麻風及結核性膿胸,其治麻風的劑量,曾有分爲每日g壹次煎服、每日g二次分服、每日g三次分服等三種,而其療效亦隨劑量之加大而提高。 至于治療結核性膿胸,亦需每日用g左右,奏效始著,服後能使膿液減少、變稀,血沈率降低,連服3個月,瘡口即逐步愈合。如果只用常用量,是不會收效的。 八、黃連g治糖尿病:本品性寒,味大苦,善于瀉火解毒,清熱燥濕,壹般常用量爲3~5g左右,由于其性寒味苦,大量或久服,易于損胃,故常與溫藥並用,如配木香之香連丸,配幹姜之姜連散,配吳茱萸、白芍之戊己丸,配肉桂之交泰丸等。 正如李時珍所言:『壹冷壹熱,陰陽相濟,最得制方之妙,而無偏勝之害』。所以其用量壹般均在常用量上下。 近年來忘年交仝小林教授,常用黃連治療糖尿病,取得突破性進展,值得參用。他說:『黃連最苦,然治療糖尿病這壹甜病特效。我用黃連,通常劑量爲每日30g,而治療糖尿病酮症,壹日最多達g,降糖迅速。』 通過回顧性分析顯示,有35%患者減少降糖西藥的用量,30%僅用中藥來維持穩定而理想的血糖水平,許多曾經胰島素用量很大的患者,甚至完全停用胰島素,這就爲糖尿病患者帶來了福音,茲附仝教授醫案供參考: 陳某,男,36歲。年7月9日入診。因血糖升高1個月就診。患者1個月前因口渴明顯而查FBG20mmol/L,診斷爲糖尿病,注射幾日胰島素後,因工作較忙未再繼續治療。刻下症見:口幹口苦甚,飲水多,乏力明顯,汗出多,小嫂頻數,舌紅、苔黃,脈滑數。查:FBG22.1mmol/L,2hPG34.99mmol/L。 西醫診斷:糖尿病。中醫診斷:消渴。中醫辨證:火毒熾盛,耗傷氣陰。 治法:清火益氣滋陰:處方:幹姜黃連黃芩人參湯加減:黃連90g,幹姜20g,黃芩30g,西洋參9g,知母60g,桑葉30g,懷山藥30g,山茱萸30g。 調整處方爲:黃連90g,生石膏60g,知母60g,天花粉60g,西洋參9g,山茱萸30g,葛根30g,懷山藥30g,桑葉30g,大黃3g,生姜5片,患者可以服藥10劑,口渴、口苦、乏力、汗多等症狀緩解約80%,查FBG6~7mmol/L,2hPG9~11mmol/L,故調整處方爲:黃連30g,黃芩30g,知母30g,天花粉30g,葛根30g,生姜5片,繼續調治血糖。 按:患者初診表現壹派火毒熾熱、耗傷氣陰之象,並有愈演愈烈之勢,故亟需迅速控制火勢,打破火毒爲病的惡性循環。此時常規用藥恐杯水車薪,必以大劑量苦寒清火之品直折火毒,方能控制火勢,故主以90g黃連瀉火解毒,直壓火勢,並以20g幹姜顧護中陽,防止苦寒傷冒。 同時配合知母、桑葉、懷山藥等大量滋陰清熱益氣之藥,以迅速補救耗傷氣陰,防止其因火勢張而枯竭,配合黃連爲標本兼治。二診已明顯收效,火勢得到控制,因而壹鼓作氣,繼續以90g黃連,清除毒火余氛,至三診時火毒已完全控制,故中病即減,改黃連爲30g調治。 討論:以上僅是舉例而已,類似者不勝枚舉。如用大劑量的防風解砒毒,桂枝治慢性肝炎與肝硬化,木鼈子治癌,青木香治高血壓,魚腥草治大葉性肺炎,合歡皮治肺膿腫,大薊根治經閉,織殼治脫肛,等等。但就本文所列述者而言,已充分說明中藥用量與作用的關系是非常密切重要的。 中藥用量的決定,是要從多方面來考慮,但要它發揮新的作用或起到特定的療效時,就必須突破常用劑量,打破顧慮。正如孫台石在《簡明醫彀》所說:“凡治法用藥有奇險駭俗者,要見得病真,便可施用,不必顧忌。” 劑量是方劑的核心、靈魂,處方是否有效,除了辨證明確,論治得當,劑量就是提高療效的關鍵。近賢冉雪峰說得好:“凡大病需用大藥(大劑量),藥用得當,力愈大功愈偉。”因此,中藥用量與作用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這也是使用中藥值得注意的壹個重要方面。 爲什麽增大劑量能加強或産生新的作用呢?這原因當然很多、很複雜。但總的壹個方面,是否可以說是符合“量變質變”的法則呢?從這壹法則的推演,可能會發現更多的藥理機制,發揮藥物的更大作用。 不過,加大劑量必須在壹定條件下,在壹定限度內確定,才能由合理的數量變化,引起良性的質量變化,否則缺少壹定的條件,超過壹定的限度,這種量變轉化的質變,就會由好事變爲壞事。産生不良的作用或嚴重的後果。 例如槟榔用75~90g是起驅蟲作用的,但如再增大劑量,患者的機體適應能力將不堪忍受,而出現休克或嚴重的後果。 明?張景嶽在其《景嶽全書》中曾說:“治病用藥,本貴精專,尤宜勇敢……但用壹味爲君,二三味爲佐使,大劑進之,多多益善。夫用多之道何在?在乎必賴其力,而料無害者,即放膽用之。”是可以作爲我們參考的。 增大劑量,不是盲目的、胡亂肯定的,而是根據古今文獻資料線索的引申,或是民間實踐經驗的事實,通過臨床實踐、系統觀察才提出的。例如用大量荠菜之治尿滯留,壹方面民間流傳有此經驗,壹方面現代藥理分析,證實它有直接興奮子宮、膀胱等平滑肌的作用,所以使用它治療尿滯留是合理可靠的。 又如夏枯草之治肝炎轉氨酶升高,是從它善于清泄肝膽濕熱、散郁結、補肝血之功能而推演,並經臨床實踐,才提出應用的。所以加大用量,不是憑空臆測,而是有線索依據,引申演繹,經過實踐觀察,方始確定和推廣的。 中藥加重用量,産生新的功能,發揮它更大的作用,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但在具體應用時,還必須辨證論治,因證選方,隨證加味,不能簡單草率。例如用益母草之治腎炎水腫,隨證加味,奏效始佳。這是使用中藥的壹個關鍵,如果忽視了這壹點,將是最大的、原則性的錯誤。 最後還要說明壹下的,就是增大藥物用量,使之發揮更大作用,要有選擇性、目的性地進行,不是所有藥物加大了劑量,都會加強和産生新的作用;同時,也不能因爲增大劑量可以加強藥效,就忽視了小劑量的作用,形成濫用大劑量的偏向,既浪費藥材,增加患者的負擔,更對機體有損,這是必須防止的壹個方面。 因爲療效的高低與否,決定于藥證是否切合,所謂“藥貴中病”,合則奏效,小劑量亦能愈病。“輕可去實”“四兩撥千斤”,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戴複庵說:“二者之論(指太過、不及),唯中而已;過與不及,皆爲偏廢”,是辨證的持平之論,值得深思。 振海堂健康管理ZHTGYG白癜风有什么症状北京有治白癜风的吗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aijiaoa.com/hjyx/571.html
- 上一篇文章: 每日一药地榆
- 下一篇文章: 33最全中药歌诀,快收藏